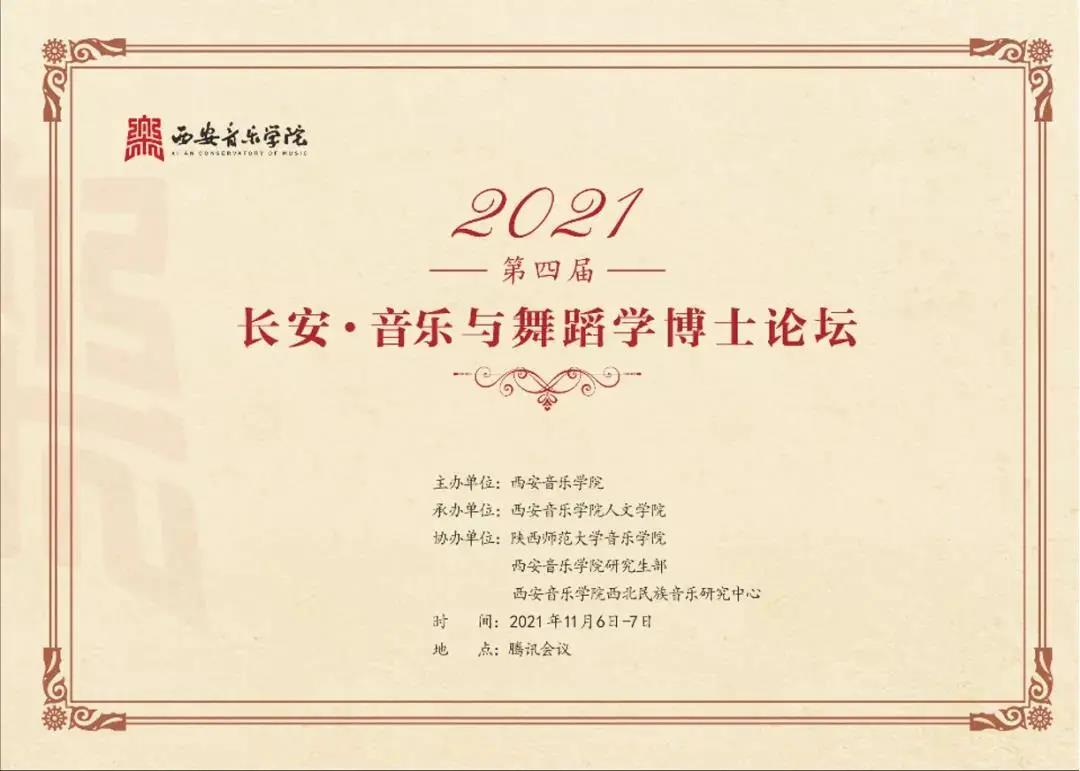
时间:2021年11月6日 9:30—10:20
题目:《口传·表述·认知·场景——黔东南雷山苗族芦笙音乐的习得过程研究》
发言人:欧阳平方,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武汉大学在站博士后。
按本届论坛学术委员会在众多提交的论文中,选择该篇论文作为主题发言,原因有二:第一,研究者在深度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从局内人的音乐用语和行为出发,探讨了黔东南雷山苗人在日常生活中习得音乐的过程与方式,使研究深入至局内人的观念与认知层面,对于当下民族音乐学界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第二,研究者深谙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与道德伦理,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性表述,体现出一名青年民族音乐学者的职业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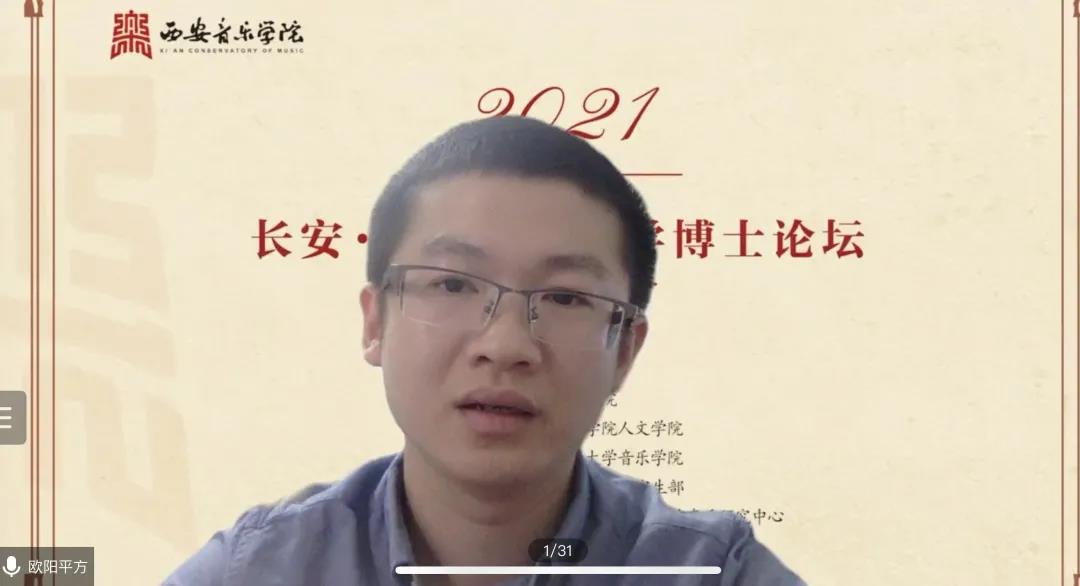
欧阳博士的研究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黔东南苗族音乐文化的客观事实,即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有一套以苗家人歌唱、演奏及演绎为核心的用乐实践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用乐实践中所使用的音乐“用语”和行为体现。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认知研究转向。如何对“活态”传统音乐事象进行描述、解释?如何理解民间艺人头脑中的音乐思维方式?这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需要转向并聚焦于语境化、过程化、身体化等方面的音乐文化认知分析。
该发言将目光聚焦于黔东南雷山苗族芦笙音乐,以苗家人的芦笙习得过程为切入点,通过对其中芦笙形制构造、指法记忆、用语表述、曲调习得、演绎过程等方面的阐述,探讨了雷山苗家人的内在音乐观念与认知模式。欧阳博士认为,这一习得过程中的“口传心(身)授”方式是一种“过程性”的“口传文本”,苗家人唯有在特定用乐场景中通过长时间的“聆听”、“模仿”和“身心实践”,才能在苗族芦笙音乐习得过程中获得感知。
通过对“苗族芦笙制作技艺”国家“非遗”传承人莫厌学、芦笙乐师杨光庭的田野访谈,欧阳博士发现苗家人拥有自己的芦笙分类体系,其独特的芦笙形制塑造了苗家人的声音审美观念与指法记忆。继而从文化表述和认知角度的对苗族芦笙的管名、唱名、演绎形式用语,以及用语表述的民间释义进行详细阐述,并以“芦笙说话”为例说明了苗族芦笙的曲调习得、生成机制和用乐场景,阐释其中所蕴含的苗家人的内在音乐思维方式和音乐文化认知。
由此欧阳博士认为,在苗家人的芦笙音乐习得过程中,既有“内在层”的音乐观念彰显,亦有“外在层”的音乐行为呈现,还有“宏观层”的音乐文化场景映射,是一种鲜活且富有内涵的“口传文本”显现。
最后,欧阳平方博士强调,学者应该在深入田野之时,充分尊重苗家人的主体性文化表述,对其“口传文本”进行客观性记录。同时反思自身文化经验导致的“认知前见”,认为进入苗家人芦笙用乐认知场景,是体验和探讨苗族芦笙音乐习得过程文本的重要途径。
评议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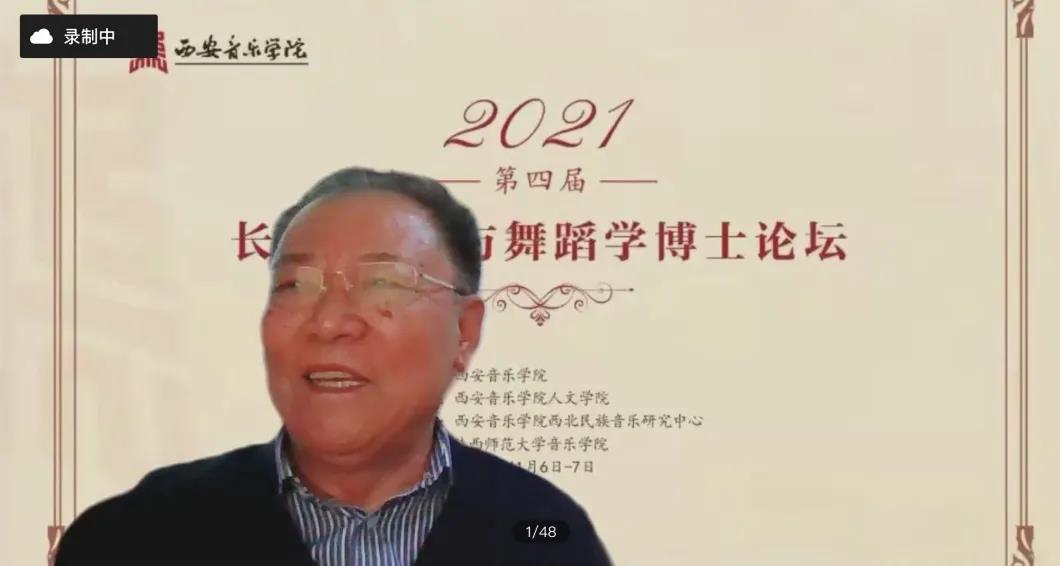
乔建中教授对欧阳平方博士宣讲予以肯定:
“该论文抓住了苗族文化中最核心的一个现象,即芦笙和它演奏的音乐,用口传心得的观念全面地解释了芦笙及音乐……这篇论文在口传心得方面,以芦笙为介入点进行深入研究,期待在他日后的研究中描述能更深入、视野更广阔、提供更多的参照系,让我们对苗族芦笙文化有更加广泛深入地认识。”
1.学术上的传承:
“1999年我曾先后到访黔东南、黔西北等地,很多苗族体系都有芦笙,因而研究芦笙是解开苗族文化的一把钥匙,而且具有值得挖掘的空间。其实,对于苗族芦笙、苗族民歌的研究,早在1957年4月—7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简其华等4位老师,就曾在黔东南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田野考察,然后写了两本著作,分别是《苗族民歌》和《苗族芦笙》。当时的研究所对整个少数民族还处于取样的状态。1999年我去考察时,就有意选择了当年这些学者所去的地方……除此之外,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的很多老师也一直在做相关研究。我觉得前辈所做的工作对我们后来学者的研究有很大影响,所以今天欧阳平方博士在前辈的影响下选择了这一题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研究观念与记录视角
“现在的研究观念方法、记录角度都(与以前)不同了。当年我们主要是把本体(音乐形态)记录下来,而今天,比如欧阳平方的论文主要通过乐器和口传方式、通过大量的田野资料来解释这些乐器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这样做是非常好的。总体来讲,芦笙歌、指法、管名唱名以及芦笙词等在研究中提到的内容,以及期间运用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方法结合“用语”的讨论等都非常详细。”
3.关于“口传”
“我觉得口传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他(欧阳平方)前面所提及的掌握芦笙演奏技艺或者掌握基本类型、曲目唱法等方面;另一部分就是进入实践活动以后,欧阳所说的表演场景,应该说这是口传习得更为重要的部分,因为还要通过民俗、各种节日等现场的方式,使乐器进入到(局内人的)日常活动场地,进而获得乐器演奏的技能,及其苗人许多体验与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习得是更重要的……。”

萧梅教授对欧阳平方论文的评议,并谈及自己的一些体会:
“一方面,这篇论文写得很好,关注的问题也很重要。近年来有一批博士论文是建立在非常扎实的田野基础之上完成的。当然,田野的同时也要有进一步的理论提升。一定要明确,田野并不仅止于搜集资料,从学科角度来讲,更重要的是要在收集资料和理论思考之间进行不断的反馈,在不断思考的过程中,完成诠释性的内容,这就与我们的认知方法有了诸多联系。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田野目标、肩负的责任和工作,我们现在通过更为扎实的田野考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际上是“从新”去挖掘、整理民间知识,如此才能汇成对传统的认知。我很欣赏欧阳平方博士的工作,这非常符合我们做田野考察和撰写民族志的一种理想。”

谢嘉幸教授评议:
“其实一个文化有两个不同故事,一个是如芦笙或整个苗族的文化,它本身的产生过程是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所追寻,当然也包含器物和文化层面;另一个是文化承载者,也就是欧阳所说的活态的人的存在地域,这两者之间——我用一个不一定很确切的比喻——是大故事和小故事的关系。欧阳的研究对传承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记录,但是对于如何去探讨背后的文化故事,但如果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是这不够的,做田野也一定要对历史有所考察。换句话说,田野现场是由历史所带来的,而历史是怎样的,是该研究是需要去延伸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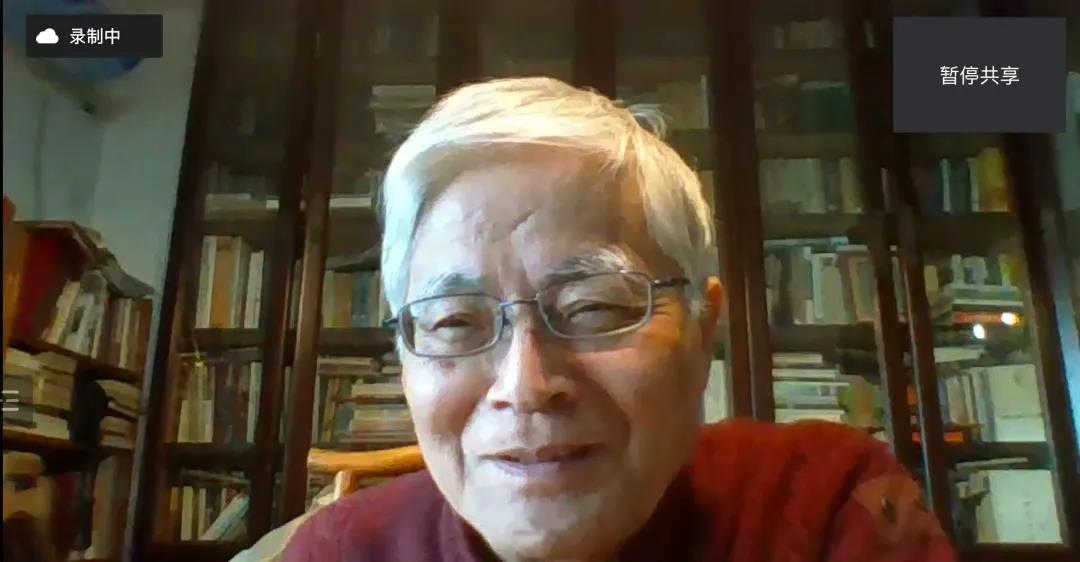
罗艺峰教授:“我对欧阳博士的论文和发言非常感兴趣。首先,他的研究展现了发散思维和内聚思维两个层面,以及二者的互相关系。所谓的发散思维就是指涉及了多个学科、多个层次;内聚思维是指研究始终落实在苗族笙的文化和相关事象上面,这是他在思维方式方面的重要特点。”
“另外,有两个问题日后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是如何处理好你(欧阳平方)的“前知识”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方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课题。另一个是欧阳提到了苗族民众对于他们的音乐认知、音乐经验并不自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心理学问题,此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最后,在研究中运用了许多苗人关于笙的词汇,是从语言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那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些非常重要的语词,在社会发展中很可能会慢慢消失。我的一个认识是语词的命运其实就是人的命运,如果我们学者可以保存下来,给未来的人留下一点儿他们当年命运的记录,那不是更好、更有价值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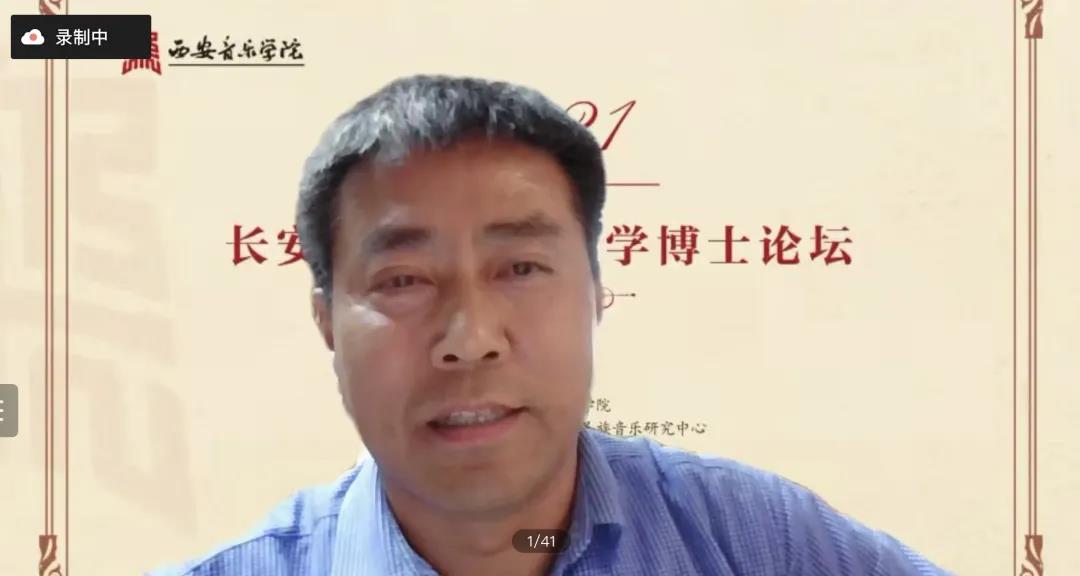
李宝杰教授在谢嘉幸教授评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明:“这两个选题,一个是在观察当下存活的意识,一个是观察失去的意识,但无论哪种都会造成自我语境的建构,且在这种语境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怎样对历史的存在进行还原,还原到什么程度,(被)还原的和历史之间又是什么关联,我们今天的研究又该如何去取位?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中间,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像当地人(局内人)那样拥有从小浸染的文化体验,所以我觉得研究者对自我建构语境的自我批判,是研究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方面。因此,我觉得无论研究文本还是研究活态内容,一定要和现实存在关联起来。”
李仁往同学向欧阳博士提问:“因为音乐只是音响,表达方面并不具体,所以,我想问的是,芦笙在表达它的语言时,在音乐方面是否有更具体的体现呢?比如您提到它的旋律和语言的音调很像,那么除此之外,在音色、音强、演奏的姿态等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体现呢?”
欧阳平方博士答:“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在研究当中可能没涉及太多音色方面,因为它“以乐代语”的这种现象主要是体现在当时所唱的芦笙歌和用苗语唱出的芦笙词当中,那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声调进行研究。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语用的环境中,这些曲调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必须是在具体场景中才能适用。此外,身体动作也是比较重要的,是重要的表述方式,因为芦笙乐舞是歌、乐、舞一体的形式,所以语言声调和演奏姿势是一体的,它们是一种对话交流的形式。”
